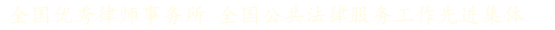点石文章|段胜亚律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谦抑性思考——以涉罪大学生行为人为例(上篇)
来源: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时间:2023-6-28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增设以来,涉及该罪名的犯罪数量激增,之前大量信息犯罪的帮助犯被单独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涉及“两卡”的案件占比极高。在涉及“两卡”的帮信罪案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很多行为人的身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将自己的银行卡、信用卡、身份信息出借给他人以换取相应酬劳。大学生因其社会经验浅薄、法律意识淡薄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及犯罪。刑法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惩罚犯罪,针对目前大学生屡涉帮信罪的现象我们需要将该罪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进行讨论,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校大学生;明知;主观方面
一、引言
(一)问题缘起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将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独立成罪。在裁判文书网上对涉帮信罪案件检索后发现,2019 年涉罪案件仅三百多件,2020 年跃升至两千余件,2021年达两万件,2022年案件数量虽有所回落,但也达到了一万四千多起。随着“断卡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司法机关处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量激增,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重视,那就是部分帮信罪行为人的身份是在校大学生。相较于其他身份类型的行为人而言,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人的获利往往相对更低、犯罪行为模式简单,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
大学生虽然是法律层面上的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就该群体的成长经历、社会阅历而言,他们生活在象牙塔里,生活轨迹单一、成长环境简单,新闻媒体近期经常用“清澈愚蠢”来形容当代大学生群体,充分体现大学生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相对较弱的特点。刚刚步入校园的大学生,承担着来自家庭的希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开启大学生活,但是因其社会经验不足、防范意识不足而涉帮信罪犯罪,误入歧途,令人十分惋惜。
学校的安全教育、基本法律知识普及对于防范大学生涉帮信罪犯罪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大学生行为人,对于刚刚开始人生新旅途的天之骄子,司法机关在处理大学生涉帮信罪犯罪案件时除了根据帮信罪的定罪量刑标进行处理外,应当考虑到刑法的目的、行为人身份,尤其需要引入刑法的谦抑性进行思考,给这部分特殊身份的行为人以正确处理,以达到刑法的立法目的,发挥刑法教育与惩罚的作用。本文针对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人的特点,将帮信罪与刑法谦异性相结合,讨论帮信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二)刑法谦抑性概述及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特点的总结
谦抑性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刑法的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体现并实现于刑法运行的全部过程。刑法的谦抑性的本质在于保障人权,限制刑法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干涉和侵犯,这就要求将适用刑法限制在必要的最小范围之内。刑法具有补充性,刑法的发动应当以其他法律或统制手段的无效为前提。
通过对涉大学生帮信罪案例的检索分析,大学生犯帮信罪的手段涵盖了两大类,包括提供互联网接入、国内互联网转接、服务器托管和网络通讯支持等高级技术手段,也包括通过使用自己的微信为诈骗犯罪嫌疑人解封微信、出售出租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电话卡等较为低级的方式。从行为类型的占比分析,低级的行为模式占大学生涉帮信罪案件数量的绝大部分。
大部分的大学生行为人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获得出借“两卡”、身份信息、出借个人微信等以换取酬劳的信息,或者从同学、好友处得知上述信息,便将自己的“两卡”、身份信息出借给他人以获取酬劳。从获利模式分析,大学生帮信罪行为人的获利不同于帮信罪通常的大额获利,一般也不是一次性获利,获利模式一般为分期获利,且总体上讲获利总额较低。
涉帮信罪的大学生,通常没有犯罪目的或者缺乏违法性认识,他们在进行犯罪行为时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出于获利的目的,未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法律风险等进行认真思考。因此在大学生涉帮信罪的定罪量刑过程中需要从行为人的身份特殊性、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刑法的立法目的、刑法的谦抑性及宽严相济的刑法政策进行综合考量。
(三)大学生涉帮信罪定罪量刑关于“明知”的考量
大学生涉帮信罪的定罪核心要点就是帮信罪构成要件中“明知”的考量,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明知的规定在刑法总则第14条,根据法条表述,行为人构成明知需要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谓认识因素,就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判断;意志因素,就是行为人希望自己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总的来说,刑法总则中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中,明知是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概括性规定。刑法分则中关于各个具体罪名罪状中的的明知是为了落实刑法总则关于故意的认识要素要求而作出的提示性、差异性规定。
就帮信罪而言,《刑法》第287条之二罪状中要求帮信罪的行为人在提供进行犯罪活动时,应当明知自己提供的帮助是帮助他人实施网络犯罪。对于被帮助行为人违法行为的明知可以倒推出行为人对自身帮助行为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危险程度的认识情况。
帮信罪是将帮助行为正犯化,此时的网络帮助行为已经具有独立的地位,该罪行为属于事实层面的实行行为,不再受共犯从属性的限制。帮信罪虽然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但是依然要对被帮助人的犯罪行为有明知,这种明知并不需要认识到被帮助者是否着手了犯罪行为,也不要求其对于犯罪进程有完整把握,而是一种认识的程度要求较低的明知,对被帮助者犯罪行为有概括性认知即可。
对于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需要结合具体的行为进行讨论。对于出借个人信息、出借两卡此类低端的帮助行为,大学生的违法性认识一般是欠缺的,那么对于该类行为主观方面的认定就需要进行“推定”,在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进行推定时,可以结合行为人的其他行为特点进行综合认定。
二、现实困境:实践中对于“明知”的推定无固定标准
(一)该罪的“明知”与共同犯罪的“明知”的关系
我国对于共同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有双重要求:一是概括性认识要求,即帮助犯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正在帮助他人进行犯罪活动;二是行为性质要求,即要求帮助犯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犯罪结果的发生上有促进作用,自己提供的行为可以对被帮助人犯罪结果的发生起积极效用。
在明知的认识对象上,行为人的“明知”与帮助犯的“明知”有联系存在,这两个明知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被帮助者的行为性质、正犯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本身提供的帮助行为的具体内容以及自己的帮助行为未来会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促进作用。
需要注意是,帮信罪中行为人只要知道自己在帮助的对象是犯罪行为,不需要“明知”自己帮助犯罪具体呈现什么样的侵害模式和构成的具体的罪名,而帮助犯要求对帮助者实施何种具体的犯罪行为要“明知”。从这一层面来讲,帮信罪中对于明知的具体要求在程度上要低于我国刑法总则中对于共同犯罪帮助犯的主观要求。其次是帮助犯要求正犯与帮助犯之间存在意思互通的联络,要求彼此之间对于犯意有沟通,共谋实施犯罪行为,而帮信罪对于明知的规定并没有此规定。
在明知的认识程度上,根据一般性规定,共同犯罪的帮助犯的主观上要明确知道自己帮助行为会对什么样的犯罪事实起到促进作用,而帮信罪的认识程度略低于共同犯罪的认知程度,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提供技术类支持在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即可。虽然该罪明知与共同犯罪的明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重合,一个行为既构成该罪,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共同犯罪,根据该罪的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量刑标准上,帮助犯的量刑通常较帮信罪更重,司法实践中往往以帮助犯予以刑事处罚。
对于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人来说,根据对帮信罪主观方面“明知”认识的标准,并不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帮助的上游犯罪是具体种类的犯罪行为,只需要对行为是违法犯罪有基本的认识即可。如果根据可能涉帮信罪大学生行为人的社会阅历、获利数额等方面无法推定出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明知”的,那么就不能对该部分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具体认定。
帮信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一般采用推定认定的方式,对于大学生行为的主观方面采用推定认定时应当综合大学生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案涉金额、具体行为进行综合考虑。大学生行为人群体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社会经验简单、风险防范意识浅薄、法律知识欠缺等。对于大学生行为人群体定罪量刑的考量并非违背刑法的平等原则,而是充分考量刑法谦异性,针对不同行为人、不同犯罪群体的特点、帮信罪定罪量刑的模式等,以达到准确定罪量刑的目的,实现刑法的惩罚犯罪与教育作用,实现刑法的目的。
(二)“明知”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
帮信罪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多采用了法律推定进行认定的方式。笔者通过对比涉及帮信罪的案件的辩护意见发现:律师在为涉帮信罪的行为人进行辩护时多采用无罪辩护的辩护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认为自己的当事人对于自己帮助的犯罪行为本身并不知情,当帮信罪的主观要件不被满足时,就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
律师的辩护主张基本包括:被帮助行为人隐瞒犯罪事实,提供帮助行为人对于被帮助人的犯罪不得而知或者提供帮助行为人仅进行正常业务行为,与其他行为人之间并没有犯意联络等等。在打击“两卡”犯罪期间,一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人将自己的银行卡进行出售,获得了一定的报酬,之后就涉帮信罪犯罪,很多行为人在心理上和事实上都难以接受。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可能仅仅是想多一些生活费,被低成本、高收入等话术欺骗、利诱,就将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卡、信用卡出借给他人,以换取部分零花钱,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其本身并无犯罪或者帮助犯罪的目的。
实践中,定罪量刑讲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涉帮信罪案件定罪量刑除了依据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外,还应根据刑事推定进行判断。在我国,很多司法解释中都选择采用刑事推定来判断涉及某罪名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属于明知。在考虑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明知是会结合社会大众对于某情况的认知程度、行为人具体犯罪行为、衍生行为等因素。帮信罪的特殊性意味着涉该罪案件中必定会出现使用法律推定认定案件事实。《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该罪的“明知”的推定:允许行为人“自证其清”即当行为人能够对自身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时,且其提供的解释能够推翻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不认定其主观方面成立明知。比如,当行为人提供的帮助行为存在明显的不合理高价时,如果行为人能够对自己提供服务的高收费进行合理说明,推翻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此时就认为其主观方面并不存在明知。
笔者认为,大学生涉帮信罪的案件,大学生行为人可以适当降低“自证其清”的门槛。比如,部分大学生在出借身份信息、银行卡、信用卡时,仅知道对方是将自己卡用于行政违法行为时,那么就不能认定该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明知”,因为此时行为人对于自己帮助行为的性质仅达到了行政违法的程度,并非是犯罪。但是也要考量到大学生涉帮信罪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对于复杂的涉帮信罪行为,如帮助他人设立境外违法网站等行为,行为人在进行违法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有了清楚的认知,此时就无需再让该部分行为人“自证其清”,那么就不需要对该部分行为人的特殊身份进行额外考量。